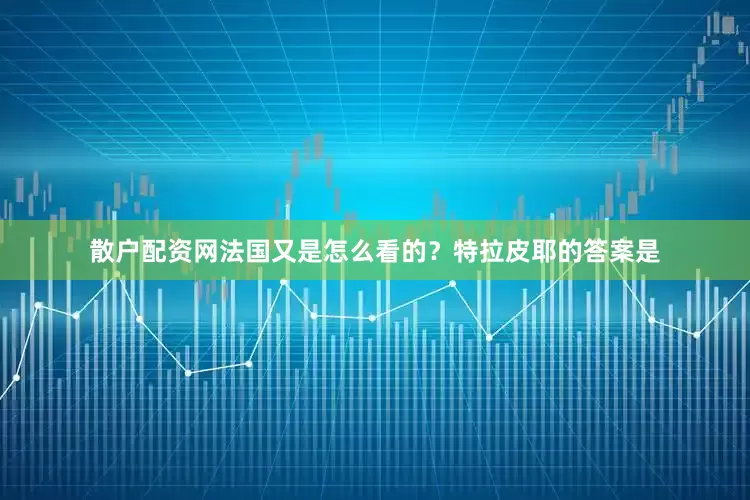电视片《回望梁启超》共五集,其内容对梁启超前期的戊戌变法、再造共和与巴黎和会着墨甚多,轰轰烈烈,然而对其后期生涯——尤其是清华国学院时期——却处理得相当潦草,仅以几段轶事匆匆带过,实为虎头蛇尾。若制作方能采访笔者,笔者定会指出:梁启超的后期不仅辉煌,且蕴藏着更大的可能性!

创作于1919年的《欧游心影录》是梁启超思想转向后期的关键节点。此书借助其拓展的世界视野,促使他在价值观上实现了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明确转折。他不再简单视西方发展为单一历史趋势,而是深入剖析,认识到西方本身即是多种矛盾价值的综合体。
书中,梁启超描绘了西方思潮的深刻矛盾: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、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、唯物论与唯心论、自由与平等等多重冲突激烈交锋。这种“世纪末”的迷茫与冲突感,让他反思西方文明的局限。

正是基于这种多元、非本质且充满内在张力的西方观,梁启超自觉步入后期。欧洲之行,特别是身处战后萧索的巴黎,结合其长期办报积累的西学通识,使他蓦然回首,对自幼熟稔的本土文化价值体系产生了惊喜的再发现。其思想动机由此超越单纯为民族国家“寻富求强”,上升为一种面向全人类的交互文化使命:“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,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,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。”他坚信发挥本国文化特质至关重要。
促成梁启超后期思想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:
亲历欧洲的幻灭: 一战后欧洲的衰败景象,现代派艺术的悲观气息,以及“世纪末”心态的蔓延,使他得以重新审视严复等人对西方的片面介绍。他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与“生存竞争”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,导致了贫富鸿沟、强权政治乃至世界大战。
巴黎和会的刺痛: 作为五四风潮的直接推动者,他痛切感受到西方在理想宣言与现实政治间的巨大落差,对其曾欲追随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间距感。他清醒认识到列强觊觎中国,强调自强才是根本,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,并呼吁释放被捕学生。
世界都市的多元氛围: 巴黎等国际大都会的多元文化混杂,促使任何置身其中者反思本土文化价值。战后世界对东方文化的普遍好感,更强化了这种反思。他甚至亲闻西方学者如赛蒙氏感叹“西洋文明破产”,寄望于中国文明救赎。
对科学主义的再定位: 他反思科学万能论的弊端,指出其导致人生机械化、物质化,虽带来物质进步,却引发精神灾难,认为“科学破产”是当时思潮变迁的关键。
交互文化哲学的理性: 他的文化回归并非列文森所言的情感依恋,而是基于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学。他认同大哲学家蒲陀罗的观点:发挥本国文化特质,并与异质文化化合,方能产生新文明。国民首要责任是光大自身文化。
少时传统的唤醒: 张荫麟指出,欧战后西方知识界的迷茫,将视线转向东方寻求解药。梁启超适逢其会,受此氛围影响,确信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医治东西方的良方,归国后遂以昌明文化为己任,尤致力于史学。
对进化观的重审与儒家“脱毒”: 他反省盛行的天演论,修正进化观。认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未必带来人类幸福,真正的“进化”应属于精神文化领域(“文化系”),放弃了早期工具理性的进化观,转向价值理性尺度。这也与民国初年儒家思想在遭摒弃后,社会反而出现退化迹象相关。
孔子生平的深层指引: 最重要的内在因素,或许源于儒家先师孔子生平的强大示范。正如孔子早年周游列国参政,晚年退而著书讲学,这两个阶段相互激发,缺一不可。梁启超后期转向学术,正是遵循了这种儒者生命周期的内在逻辑——从积极参政到退而结网,升华精神,成就名山事业。这体现了他力图提升民族文化自信,同时以开放心态主张中西文化“化合”,反对文化独断主义。
遗憾的是,国内外研究者常受限于意识形态、教育背景或狭隘的学科分工,难以同情理解梁启超后期的意义。他们或将其视为天生的政治家(后期是政治失意的退隐),或视为纯粹的学问家(前期政论粗疏),如徐铸成认为其后期“与世两忘”,桑兵认为是为研究系培养人才。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,割裂了其作为儒者/通人生命历程的统一性。
梁启超回归学术,虽有国际幻灭、国内混乱等外部刺激,但根本源于其儒生性情对孔子风范的本能追随。这种文化本根的再体认,是其后期关键选择(如修复与康有为关系)的基础。他后期强调“舍西学而言中学者,其中学必为无用;舍中学而言西学者,其西学必为无本”,主张“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”、“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”,正是李大华所总结的:在时代与民族观念交叉中,提高民族文化自信,以开放心态推动中西文化“化合”,反对独尊。
清华国学院:进取的蜕变与未竟的伟业
因此,理解梁启超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志向至关重要。他充满激情地来到清华,绝非遁逃或败退,而是其生命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。他需要一个话语场整理、激发其欧游后的思想发现。
对于梁启超这样深谙儒学的人物,孔子晚年讲学著书的模式极具吸引力。《欧游心影录》的写作,正预示其生命后期的开启。清华国学院为他提供了理想的平台。他视教育为快事,在《教育家的自家园地》中生动描述了教书育人的喜悦与收获,认为这是“占尽便宜”的事业。
清华国学院亦因梁启超的加入而声名鹊起。其健笔的影响力、为官经历转化的人脉与名望,在当时无出其右。他的讲学极富感染力,梁实秋、熊佛西均生动记载了他全情投入、手舞足蹈、令听者动容的场景。他与学生间既威严又融洽的师表风范,体现了中国书院教育的精髓,是国学院成功的神话秘诀之一。

在此环境中,梁启超为自己设定了宏大的著述计划(如规模超越韦尔斯的《中国文化史》),并已着手。更关键的是,其学术环境与交谈对象(王国维、陈寅恪等)已从报章转向最高学府,预示着其思路将更趋缜密、论证更为厚重、成果更趋学术化。他的研究将继续结合西学视野、关怀国是民瘼、依托中国文化本根,与时俱进。
梁启超是罕见的百科全书式通人,契合中国文化对“通人”、“完人”而非狭隘专家的要求。唯有他,有能力撰写贯通磅礴的文化史巨著。然而,一次医疗事故(源于对西医的盲信)残忍地终结了这一切可能性!

试想孔子若仅享年56岁,未及著书讲学,其“万古长夜”之评焉存?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短暂后期,是一场极具浮士德色彩的悲剧——不仅是其个人的巨大损失,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。若天假以年,以他的学识、精力、阅历、文思,其学术成就不可限量;其在清华的讲学育人事业,潜藏的可能性或许更大。
他所展示的可能性——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估中国古文化价值,并以此重建独特生活世界——正是清华国学院(无论过去或未来)应继承并完成的伟业。梁启超未竟的后期事业,至今仍需后人一以贯之地追寻。
汇盈配资-股票网app-配资证券网-配资炒股app最新版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